
打從2009年開始,我便將自己每次跑馬拉松的經歷都寫成報告,發表在我的個人網誌裡,不經不覺在這八年間已寫了26篇。然而2017年的芝加哥馬拉松已過去了差不多一週,我卻始終提不起勁去回顧這次比賽。究其原因,或許多少是與自己差勁的成績有關,但更重要的理由,卻是我已無法再從撰寫賽事報告的過程中感受到樂趣了。
這份帶點厭倦的感覺可能跟馬克‧吐溫在自傳裡描述自己在密西西比河學懂掌舵後的情況相似。他說:「現在我自信已掌握到這條河流的語言了,我熟悉它一切芝麻綠豆的特性,就像我對26個英文字母滾瓜爛熟一樣,我從中學到的東西確有很多,然而我也同時失去了另一些東西,而它們更是我此生永遠都追不回來的。這條壯麗河流曾令我感歎的優雅、美麗與詩情畫意都已一去不復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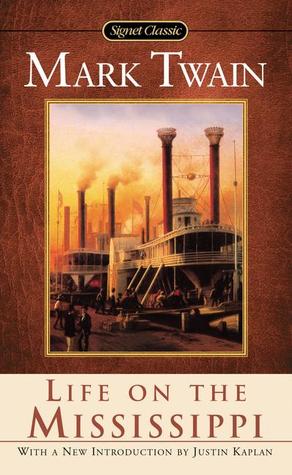
馬克‧吐溫在成功駕馭密西西比河後卻不再覺得河流吸引,單憑他這番說話,我們便可以斷定他並非一個情種。因這番說話所顯示的態度,無疑就是暗示追到上手的女人便已失去她原來的嫵媚動人。這種大男人心態顯然是極膚淺的,他忽略了河流總是善變的特性,正如男人膽敢小覷女人的喜怒無常一樣。何況西洋謬語不是也有說過:無人能腳踏同一條河流兩次,因這已不是往日的河流,而你也不是往日的舊人嗎?
所以若然馬克‧吐溫覺得密西西比河對他已喪失了魅力,或我感到撰寫馬拉松報告已變得很沒趣的話,那敢情就是因為我們都被某些規則與格式綁架了想像力。他老人家大概是被一大堆操作船舶的守則綑綁了吧,而我則被困於往日習慣了的書寫格式,如此昔日曾使我們樂在其中的嗜好便慢慢退化成不斷重覆的例行公事,要擺脫困境,重拾趣味,恐怕還是要我們自己肯走出框框。
想通了這一點後,我便打算不依格式地去寫今次的比賽。我不會再平鋪直敘地去講我從某處到某處看到了的風景,或細數我從某地到某地經歷過的事情,而是會不拘一格,隨心所欲地去東拉西扯。我希望情況會像我與你偶然在酒吧中踫頭,大家聊起上週我剛走完了一趟的芝加哥馬拉松,然後我覺有某些事情可以向你吹噓,便恬不知恥,像個關不掉的水龍頭一樣高談闊論起來。你可能會基於禮貌而向我頻頻點頭,但其實我那管你愛不愛聽呢,我只要自己聊得興奮才要緊嘛!
外套亂飛
看到芝加哥馬拉松起跑前毛衣與外套在空中亂飛的狀況,不知道港產的環保先鋒會有什麼感想。他們又會想出來仗義執言嗎?或是起碼會在社交媒體上抒發感情,慨嘆馬拉松比賽簡直是一場地球生態大災難?

要解決跑手起步前保暖的需要而又要同時減少丟棄衣物,據說是有許多創新方法的。我見過有環保衛士建議我們可以將外套綁在腰間,全程帶著它來跑步。但那顯然是會影響速度的,何況挺著一個溫暖的屁股來跑步也要冒上生熱痱的風險。我又見過有人提議大家可以將透明雨衣摺好後收進小腰包,但我懷疑提出這建議的人其實從沒試過將一件穿著過的膠雨衣摺好再收藏,在戶外而且人多擠擁的環境中你只會將它綑成一團,要收納起來你會需要一個背囊。
我相信自己是個會尊重環保的人,但也同時體察到人存在的本身就是個現成的污染源,當人有慾望要滿足,就必然會有相應的資源消耗。至於某個慾望是否有價值去追求,資源又有否被濫用等問題其實都可以討論,然而每秒鐘世界紀錄的突破其背後也以無可計數的資源消耗來支撐,我這等平凡人雖沒破世界紀錄的指望,卻總會懷著突破自己的願望來投入比賽,所以我不諱言,自己也有將一件舊長䄂外衣丟在芝加哥千禧公園的路旁。
這時候我身旁還站著一位脫去了白色運動外套,露出黑色 Bra Top 與運動短褲的金髮女郎,作為響應環保的一員,自然明白到壓抑慾望的重要性,所以我要自己眼望前方避免分心,然後起步的槍聲不久便從前方響起來了。
賴地硬
以前間中聽到有香港人說渣馬賽道被大型貨車輾壓得凹凸不平的投訴,但要體驗真正的破爛嶙峋,你還當真要來芝加哥觀摩一下。裂縫足有成寸闊的柏油路、經修補後凸起來一塊而又不規則的路面、與及古老鐵橋上網狀的小洞等(雖已鋪墊了紅地毯),在在都顯示芝加哥確實是個擁有悠久歷史的美國城市,但如此路況,卻令跑手在比賽時都要格外小心。

一直以日版 Skysensor 征戰四方的我,首次在20公里後感到鞋底的保護不足,也不是想要「賴地硬」,卻只是難以想像那些穿五趾鞋或赤足跑的朋友如何能捱得下去。
古惑領跑員
我懷疑這班傢伙根本就不是大會提供的領跑員,雖然他們身後都扣上同一款式的時間牌,上面也印上了 Nike 的商標,有些領跑員的手上還舉著一支以小棍子豎起來的牌子,上面印有明確的目標時間,如此一來,便似是值得大家尊重的權杖了。但事實上他們身上與棍上所標示的時間,卻都不是一個信心保證,而只是他們的個人願望而已。
以3:20作為完賽目標的我,在起跑初段緊隨兩位舉起了3:20時間牌的領跑員,但才跑出5公里後便發覺事有蹊蹺,大隊的均速根本是以接近 4:50/km 來前進,慢於目標速度之餘更絲毫沒有想要追落後的勢頭。舉起牌子的領跑者倒有頗多口水,不住叫跟隨他的朋友要放鬆心情來跑。

在仍未去到絕望階段的我便不想跟他們胡混下去,撇下他們便獨自上路。雖然我的速度在 12 公里後便漸漸慢了下來,更在 18 公里後被這班所謂 3:20 的大隊趕過,但我可以肯定,他們是無法以 sub 3:20 成績衝線的。
事實上,我最終的成績為 3:53:10,卻在最後 3 公里時才被舉起 3:40 牌子的領跑員趕過,他們在後段如何發力也不可能比我快5分鐘到終點,所以你說這班傢伙如何能稱職地領跑呢?
我愛吳京
以 3:20 為目標卻終於跑出 3:53:10 的成績,這當真是有點令人尷尬的結果。我也不是沒理由去為糟糕的成績開脫,但這時候我卻想起了吳京。
吳京的《戰狼2》在剛過去的暑假以超過50億票房收入成為了全球有史以來最賣座的華語電影。這其實是一齣合格有餘的動作片,卻因為種種原因而被香港觀眾們所忽略。在這裡我不是想要談電影本身,卻是想起了吳京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的一段說話。

----- 廣告 Ad -----
電影《戰狼2》拳拳到肉動作連場,而吳京本人也拒絕替身,全部鏡頭親身上陣。有記者便問到他舊日的傷患,吳京卻回答說:「動作演員總說自己有傷好像是有點矯情吧。」
嘩! 這說法實在是太有型了!
回想起來,自己在馬拉松舞台上演出也有十年了,雖說從沒當過主角,卻自詡是個會講演員道德的資深甘草。導演在起跑線上喊完一聲 “Camera!” 後,我都會全力以赴,傾情演出,若說因傷患而影響了表現,就該回去反省為什麼不在拍攝前好好將它處理,事到如今,難道還好意思在搞砸後撒嬌嗎?
所以我也不打算多談自己的膝傷了,卻要承認我從18公里後都要半跑半行地前進,這在過去十年來不管我跑出什麼成績都是絕無僅有的。
但無論如何,下次我會再努力。
駛唔駛咁大聲啊?
促成芝加哥馬拉松熱烈的氣氛,除了路上兩旁群眾為參賽者打氣的喊叫聲外,更應記上一功的,便是佇立於街角朝賽道狂轟猛炸的音響喇叭了。

高分貝的搖滾音樂在路上每隔不遠便會出現,尤其當喇叭設置於賽道轉角處,而你又想以最短距離切入彎角時,便都要忍受震耳欲聾而且頗為沙啞的歌聲。忽然懷念起吐露港公路上的單車阿伯,他們的音響設備都非常有力量,而且他們都愛聽葉振棠。
紅日我唔愛你
今時誰還敢否定地球暖化的事實呢? 有早年來過芝加哥的朋友跟我說,從前九月時候已經遍地黃葉的芝加哥,卻竟然在十月的日出後還會有二十多度的和暖氣溫。

回港後上網翻查,大會宣稱比賽當日的氣溫約在 13-23 度之間,但我在賽道上的感覺卻有如在 25 度以上還被太陽一直追著烤烘一樣。歷史上芝加哥馬拉松曾在 2007 年於開賽3小時半後宣布腰斬,因當天氣溫上升至史無前例的30度以上,還導至一名參賽者死亡,50多人送院。
幸好今年大會設置的水站十分充足,清水、運動飲品與能量補充食物一應俱全,再加上我在十多公里後已放慢了腳步,便用不著在沒什麼可爭的情況下去拼命了。
Free to Run
最後我想談在我搭乘國泰航機飛往芝加哥的途中,馬拉松訓練中心的教練添哥忽然輕拍我膊頭,推薦我看一齣在航機娛樂系統上有播放的紀錄片《Free to Run》。

但與其說這部電影很勵志,倒不如說這是一部紀錄了長跑文化在過去50年如何變遷的電影。長跑在過去作為一種只有怪人與精英才會參與的運動,它試過歧視女性,亦試過頑固地要堅守業餘性質,不准運動員接受商業贊助或贏取奬金。但隨著個人主義席捲全球的大潮,所有壁壘到今天都已應聲倒下,到今日,任何人都能以任何理由,懷抱任何目標,再以任何自己喜歡的方式來跑步。任何型式的批評與干涉,反都變成了對人權與自由的侵犯。
然而自我本位壓倒一切的後果,卻是令運動變得愈來愈商品化,亦使長跑參與者對旁人愈來愈漠不關心。電影最後講2012年紐約馬拉松因風災珊迪的破壞及市政府要忙於救災而取消,卻引發大批報了名的參與者不滿與投訴,後來有人經社交網絡串連跑友於原定比賽當天照樣起跑,卻觸發往日會為跑手打氣的紐約市民變成在街上示威,他們朝著堅持要跑步的跑手們高喊:「當屍體正從廢墟被挖起來的時候,你們竟喜氣洋洋地在大街上跑步?!」
有說做人的根本就在於一個「度」字,世上沒有必然的對錯,卻有我們對分寸的拿捏。勇敢總在懦弱與魯莽的中間,堅持也在善變與頑固的中間。至於自由呢? 所謂 Free to Run,如何才算是自由自在地享受過跑步呢?

在烈陽高掛的週日中午,在芝加哥馬拉松終點在望的一段路上,我忽然想起了這個問題。能夠自由地奔跑,便應該算是一種境界吧,就在挑戰自我與不去強求的中間,也在享受樂趣與避免慵懶的中間,但至於這個中間點具體究竟在那裡,卻是一個「度」的問題,要我們用雙腳在公路上窮一生去尋找。
原文載於前璡博客
Fitz Facebook專頁
[前璡博客] 澳洲黃金海岸馬拉松2017
東京馬拉松2017
廣州馬拉松 2016
我們的毅行者2016
[100円的愛] 香港渣打馬拉松 2016
Fitz Running 跑步
